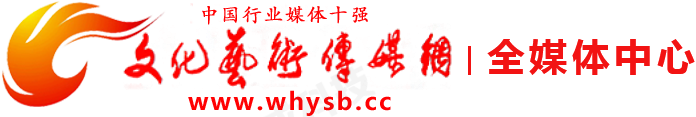書卷多情似故人
“如可贖兮,人百其身”。說的沉重一點,悼亡的話題似乎比愛情的話題還要恒久。一個人有可能一生命運遇到愛情,但是,死亡卻是無法回避的,尤其是對于國家與個人有著無可比擬重要性的人物,一旦馭鶴,唯有遺憾。《金融時報》2017年年終文化專論《慎終追遠》稱:眾多文化名家相繼去世,引發公眾普遍的哀思,是值得銘記的文化現象。文章紀念了余光中、周有光、楊潔、屠岸等文化名人。而進入2018之后,哀思還在繼續。
騎龍韻律金剛語,駕鶴英魂玉石詩
2017年12月15日晚,筆者應邀參加“第17屆(深圳寶安)華文詩人筆會”,趕到賓館已是晚上7點。報到后匆匆上電梯,只見一位老人坐在輪椅上微笑。著名詩人、《華夏詩報》執行主編洪三泰老師介紹:“這位就是創會詩人野曼先生。”我上前輕輕地握手問好。洪老師說:“野曼先生已經97歲了。”我們都很吃驚。
第二天,野曼先生坐著輪椅到達會場,宣布筆會開幕。他拿麥克風的動作并不自如,聲音也有點弱,顫巍巍的,而且,很快被如雷的掌聲所淹沒。
“華文詩人筆會”以往叫“國際華文詩人筆會”,發軔于1993年,是野曼先生與犁青、徐遲、張志民、鄒荻帆、舒婷等新老詩人一同發起,每屆詩會均邀請數十個國家的多位詩人出席,頗有影響。
沒想到那第一面次竟是永訣。
2018年1月3日晚,洪三泰老師發來微信:“深切哀悼野曼老師——騎龍韻律金剛語,駕鶴英魂玉石詩”。筆者一怔:才過了半個月!
知道“野曼”的名字是1982年。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,抗戰文學,有野曼先生1939年與蒲風主編《中國詩壇嶺東刊》的記載。著作等身的先生主編過《文藝世紀》,做過《華夏詩報》總編輯,最早的詩集《短笛》1942年出版。
初見即永訣,深夜難眠的筆者湊成一副挽聯發給詩友:“新詩報短笛吹開世紀文藝,古嶺東大愛暖透千年寶安”。
初見即永訣,無法說幸也不幸。畢竟見到了載入史冊的前輩,畢竟野曼先生的詩魂在另一個世界仍然會光彩熠熠。是的,年輕時大家都是“詩人”,但是是否真有詩心,還是要看道別的方式。
2018你1月12日,港城湛江的一家舊書店里,筆者買到了野曼先生的詩集《愛的潛流》,第一首就是歡呼進入新時期的《昭雪了》。
勒馬黃河悲壯士,揮戈易水哭將軍
據報載,1946年,重慶各界舉行追悼“四八烈士”大會,清理挽帳時,發現此聯只有上聯缺了下聯,是追悼葉挺將軍的。清理人員立即電話紅巖辦事處,得知此聯是劉伯承同志從太行山前線發來的電報,下聯為:“揮戈易水哭將軍”。
忽然記起以上掌故者,因為2018年1月9日,有兩則噩耗同時傳出:兩彈一星功臣袁承業、中國氣動彈性專業奠基人管德兩位大師、院士同時去世。黃河嗚咽,易水悲鳴。
袁先生是浙江上虞人,父親畢業于金陵大學,是有機化學家。為兒子起名“承業”,即希望“子承父業”。袁承業1948年畢業于國立藥學專科學校(中國藥科大學前身),1951年作為建國后首批公派留學生,赴蘇聯攻讀化學研究生。他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開始學俄文字母。靠一位蘇聯老太太每天輔導幾個小時俄語,頑強地學習和工作,1955年9月以優異成績通過論文答辯,獲蘇聯科學副博士學位。1959年,為“兩彈一星”急需,他毅然改行,組建并領導核燃料萃取劑研究組,成功研制P-204、N-235和P-350等萃取劑,為中國原子能工業的發展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。
然而,居功至偉的袁承業,堅持不在項目書中署名,他始終認為,祖國的尊嚴和國家的需求至高無上:“作為科學家,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也應該問問自己,我這一輩子為國家做了哪些有用的貢獻。”
嗚呼!比比花巨款投機、2009年僅僅差一票落選中科院院士的貪官、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——其兩部高端“著作”均由鐵道部官員出面,召集北京交大、西南交大、同濟大學等單位數十位教授、研究員,住北京高級飯店,突擊編寫限期完成,然后署上‘張曙光著’加急出版——人格的高下,果真能夠有無限大的距離也!
未許落花生大地,不叫靈雨灑空山
這是端木蕻良先生挽許地山的名聯。在聯里巧妙嵌進“許地山”及其筆名“落花生”,《落花生》與《空山靈雨》均為許地山名作。而且許信仰佛教,靈雨即好雨不灑“空山”,說明出世的許氏做了入世的功業。
據學者雷頤微博消息,著名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王學泰于2018年1月12日晨病逝,享年76歲。
王學泰先生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,著有《清詞麗句細評量》《中國人的飲食世界》《中國流民》《幽默中的人世百態》《偷閑雜說》《水滸與江湖》《中國飲食文化史》等多種著作,后學們從中獲益良多,正可謂“不叫靈雨灑空山”。
鳳凰網曾在2014年3月對王先生進行了長篇專訪,采訪中,王學泰稱他不喜歡被叫“知識分子”,寧可被叫做“知識人”;他說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;他說“意見領袖”是貶義詞,“知識分子約架”是文明倒退;他說中國文化平均200年動蕩一次把從前文化消滅殆盡;他說判斷文化高低的重要標準是對個人價值承認與否——善于制造“奇談怪論”的王學泰先生,文革中曾因“現行反革命”入獄數年,但是,其思考的觸角從不曾折斷。于是,作為繁花似錦的思想者,他的智慧的“靈雨”將繼續滋潤后學、滋潤古九州的山山水水。
乾坤有意終難會,書卷多情似故人。緬懷逝去的大師、學者、詩人,我們只能說:那美好的仗你們已經打過了,當跑的路你們已經跑盡了,所信的道你們已經守住了。后來者的任務只有兩個字:繼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