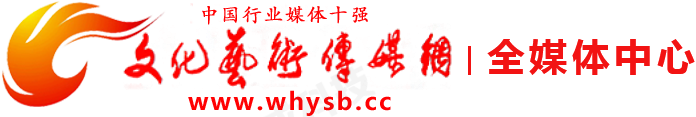桃李無言花自紅
“要求”是嚴肅的,也可能是無力的,可能是充滿了正義感的,也可能是某些人做不到的。“要求小學生睡眠要達十小時,中學生九小時”,誠意可感,天人共鑒。只是實際情形之下往往成了虛擬語氣。老詩人食指批評新詩人余秀華,提醒她關心人類的命運、祖國的未來、農民生活的痛苦,無奈余詩人本人意見很痛苦,也需要給她“喝咖啡、看看書、聊聊天”的權力。瓊瑤阿姨要求恪守版權規定,以至于年屆八旬還要“整理我的‘全集’,分別授權給大陸的出版社”,當然值得敬佩,然而盜版書至今絡繹不絕,說明其“言情”并不過時。
何來酪果供千佛,難得蓮花似六郎
這是魯迅《秋夜有感》的頸聯。“六郎”原指唐代張昌宗。《唐書?楊再思傳》載:武則天時,“昌宗以姿貌見幸,再思又諛之曰‘人言六郎面似蓮花,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,非六郎似蓮花也。’”逢迎至此,的確肉麻之至。但就“不易”立論,此聯又恰恰說明了言易行難,用時下流行語叫做“理想豐滿現實骨感”也。
進入新年第一周,有新聞曰:“教育部要求小學生睡眠要達十小時,中學生九小時,家長們怒了!”說是有司《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》再次明確:“家校配合保證每天小學生10小時、初中生9小時睡眠時間”。家長的不滿可以理解,因為京滬等地朝九晚五,孩子多半沒有午休,按照“要求”,早上六點半起床勉強還做得到,可作業如山,晚八點半休息談何容易!但有關部門同樣是一片好心,即便目前達不到,也算是有了利國利民的“偉大目標”。孩子們個個睡眠缺乏,如果規定說“命該如此”,豈不更糟糕!
此乃“已無酪果供千佛,偏要蓮花似六郎”,無可奈何。曾幾何時,“北京公布公廁管理服務標準,規定公廁里蒼蠅不得超過2只”,緊接著西安與南昌則規定“不得超過3只”。網民大惑:蒼蠅乃飛行動物,行蹤不定,斷不會趴在那里聽人查數,所以規定疑似落花有意,流水無情。被批評為“有理想,沒理性,既無知識,又無常識”的行政態度。
子曰:過猶不及。有些事可以規定,有的事則很難規定。與其滿懷善意地“定了再說”,不如先想一想:有人問一句“如何實施”咱怎樣回答?
同是肚皮,飽者不知饑者苦;一般面目,得時休笑失時人
這是清代學者、詩人朱彝尊的口語化對聯。說的是“設身處地”而將心比心。筆者卻是由此聯想到日前新老詩人的舌槍唇劍。
1月13日,著名朦朧詩人食指批評新詩人余秀華,稱她的理想生活就是喝喝咖啡、看看書、聊聊天,對人類的命運、祖國的未來、農民生活的痛苦等宏大命題視而不見。并說評論界捧紅余秀華是“不對歷史負責”的表現。而余的回應也針鋒相對,首先是說自己不知道食指是何人,而后表示自己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痛苦,并反問道:“人們向往田園生活,憑什么又鄙薄它?”
這實在又是一段“難得蓮花似六郎”的悖論。
食指先生憂國憂民,心懷大愛,本是那一代詩人最為可貴的使命感與責任感。至今堅持不懈,可見對于國家與人民“愛之入骨”。而對黃鐘大呂的呼喚,與時下的“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,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”并無二致。余秀華的“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痛苦”乃是詩人的直感,你也不能說不允許她覺得“田園生活美好”。鐵板銅琶之外,她要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”同樣是自己的自由。畢竟也要有人描寫“小橋流水人家”。
但是,客觀地評論,余詩人還是有點“勉強”了。食指的作品不僅見于各個選本,而且進入了大學講章,作為小有名氣的新詩人,理應知道。而且,余詩人自己家的圖片網上就有,慘狀令人心疼。她去溫州打工,殘疾人工廠棄而不用,買一只瓷碗學要飯又跪不下來,“那時候有鋪天蓋地的憂愁,/19歲的婚姻里/我的身體沒有一塊完好的地方”,以至于跳湖自殺——這一切哪里有半點陶淵明式的“田園生活”的影子?如果說現在余詩人有點稿費了,離婚了,有權力享受“田園”了,也請“得時休笑失時人”,中國尚有幾千萬人過著艱難的生活,國家“扶貧”的任務依舊繁重。吃不飽肚子的同胞仍然沒有“詩與遠方”,食指先生的憂慮并不過分也。
書似青山常亂疊,燈如紅豆最相思
毛澤東鐘愛的古籍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(清人梁紹壬著)載:清人葛秋生書齋懸一聯云:“書似青山常亂疊,燈如紅豆最相思。”而“亂書”與“相思”不能不讓筆者記起瓊瑤阿姨。
2018伊始,中南博集天卷與湖南文藝出版社合出最新版本的瓊瑤經典作品,定名“光影輯”的第一輯,收《窗外》《一簾幽夢》《在水一方》《煙雨濛濛》《庭院深深》和《幾度夕陽紅》。瓊瑤在新版本序言中說: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,寫出65 本書,15 部電影劇本,25 部電視劇本一千多集。我卻做到了!對我而言,寫作從來不容易……‘投入’是我最重要的事,我早期的作品,因為受到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時期的影響,大多是悲劇。寫一部小說,我沒有自我,工作的時候,只有小說里的人物。我化為女主角,化為男主角,化為各種配角。寫到悲傷處,也把自己寫得‘春蠶到死絲方盡’”。無論后人如何評價,瓊瑤對于幾代年輕人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,“純情”拿著筆“癡情”無可厚非,即將八旬而念茲在茲也彌足可敬。
而且,“亂書”不僅是說她著作等身而“四壁皆書”,而是另有隱憂:“大陸早已有了我的小說,因為沒有授權,出版得十分混亂。1989 年,我開始整理我的‘全集’,分別授權給大陸的出版社。”但愿這次的分輯出版能夠做成個“一錘定音”的“經典”。
“惠蘭有恨枝猶綠,桃李無言花自紅”。善惡功過,是是非非,且按下不表,因為時間總是公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