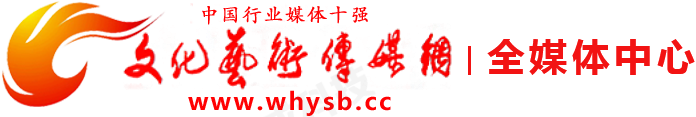文章浩氣起太初
——饒宗頤先生的啟示
2018年2月9日,陰歷臘月廿四,筆者從梅州趕往潮州。為表達家鄉人民對饒宗頤先生的深切緬懷,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在館內翰墨林展廳設立靈堂,于2月9日到12日接受吊唁。
筆者當日13點左右到達,首批吊唁者已經離去,頤園十分安靜。
與媒體上的101歲不同,大門左側的公告寫著,饒宗頤先生“享年積閏一百零五歲”。潮州籍弟子解釋曰:古習俗是3個閏年加3歲,虛歲加1歲。
翰墨林內外清凈整潔,吊唁者腳步也很輕。筆者提筆簽到,冊子上一頁是林倫倫教授的挽聯:“一代通儒才高八斗精六藝,千年師表學富五車鑄三求”。
肅穆的靈堂十分靜謐,沒有哀樂。饒宗頤先生的雕像兩側的挽聯是大字隸書:“哲人勛績千秋念,泰斗輝光萬古垂”。兩邊排列著精致的花籃。
這是筆者第三次造訪,前兩次的朝拜與求學已經為哀思籠罩。泰山其頹,哲人其萎,一個屬于傳統國學的時代結束了。再次踱步于“天嘯樓”左近的大小展室,密密麻麻的感想珊瑚般盛開,而最為迫切的是:饒宗頤先生的啟示何在?
家學:天涯久浪跡,嘯路憶兒時
這是“天嘯樓”門兩側的楹聯。
饒宗頤先生八十年如一日的做學問,起點恰恰在于家學。先生自幼便有“神童”之稱,但“神童”的兒時并不天真爛漫:“我小時候十分孤獨,母親在我兩歲時因病去世,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,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。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,一是家里訓練我寫詩、填詞,還有寫駢文、散文;二是寫字畫畫;三是目錄學;四是儒、釋、道;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。”
饒宗頤認為,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。因為有家學的便捷與“因材施教”,孩子“開竅”較為直捷。這里的“家學”,不僅是藏書豐富,父輩博學,更重要的是開啟幼童寬廣的心地,鼓勵后代斑斕的幻想,引導孩子少走彎路。
饒宗頤自幼暢游藏書之海洋“天嘯樓”中,侶詩書而伴典籍,16歲開始便繼承先父遺志,續編《潮州藝文志》,這在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。
而且,初中沒有讀完就果斷輟學,同樣得到了家庭的支持,這在今天也幾乎是天方夜譚。
或曰時下誰家還有“天嘯樓”?到哪里去找陳寅恪、錢鐘書、俞平伯們唾手可得的“家學”環境呢?
竊以為在如今學科分類之細膩、教育制度之現代的背景之下,“家學”更多的是有效的“提前教育”。60歲的退休制度,讓不少年富力強的“爺爺奶奶”成了孫子輩的朋友。有知識與精力的老人,拿出部分時間教育孫子輩,完全可以奠定孩子的學養基礎。筆者身邊有女孩去年12歲考上浙江大學者,主要是爺爺教育的成績。中國科技大少年班至今仍然人才輩出,也與家庭教育前提息息相關。近年來,中外教育家反復強調:家庭教育已經占到所有教育的80%左右。實際上恰恰是提出了“微時代家學”的問題。有學養基礎的父輩、爺爺輩掌握了教育學、心理學,完全可以充任“多快好省”的教師。而時下的數字圖書館、閱讀器等便利,也完全可以視為今天的“天嘯樓”——關鍵在于“人”的素質的教育,知書達理的教育,這是“新家學”的偉大使命。
擴而大之,今之“血緣遺傳”即“嘯路”、環境熏陶即家教,應該具有全新的內涵。傅斯年曰:“家學者,所以學人,非所以學學也。”所以,不能認為“家學”已經是“絕學”而饒宗頤先生式的學習無可師法。
華學:萬古不磨意,中流自在心
“萬古不磨意,中流自在心。天風吹海雨,欲鼓伯牙琴。”饒宗頤先生胸中千古難滅的“意”,應該就是其“三求”與古人的“三不朽”:求是、求真、求正;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
不是說聲光電化的科學不重要,也不是說博大精深的西學不重要,而是從饒宗頤的成功可以發現:其學養基礎在于立足國學的文史哲兼通。他說:“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、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,按照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,其實是文史哲相通,文中有史,史中有哲,哲中有文。”循此路徑,他才業精六學,才備九能,日臻化境。
歸納其著述,饒先生分為“敦煌學”、“甲骨學”、“詞學”、“史學”、“目錄學’、“楚辭學”、“考古學”(含“金石學”)、“書畫”等八大門類。后人亦有分為14大類者。而錢仲聯先生則從“考”與“論”切入,指出:饒宗頤的國學立足于王國維、陳寅恪等之上而站得更高:“所考釋者,自卜辭、儒經、碑版以迄敦煌寫本;所論者,自格物、奇字、古籍、史乘、方志、文論、詞學、箋注、版本,旁及篆刻、書法、繪畫、樂舞、琴藝、南詔語、蒙古語、波斯語,沉沉夥頤,新解瀾翻,兼學術文、美文之長,通中華古學與四裔新學之郵,返視觀堂、寒柳以上諸家,譬如積薪,后來居上。九州百世以觀之,得不謂非東洲鴻儒也哉!”(《固庵文錄序》)誠哉斯言。
“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,是從古人的智慧里學習東西。”故此,選堂先生的“意”無疑充溢著漢民族的國學氣息。
然而,先生本人卻對“國學”二字并不滿意:他說,各國家都有本國的文化,把中華文化稱為“國學”,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,因此,他認為稱“漢學”或“華學”更為準確。他創辦以中文為媒介的大型國際性學報《華學》并自任主編,正是為“華學”正名且流布。
所以,重視“國本”,又能會通古今中外,是“饒學”的重要特色。
由于種種原因,如今上至文科“長江學者”,下到各個大學的博導碩導,其“華學”基礎實在難以望選堂先生之項背。如今國家倡言傳統文化,實乃迫在眉睫之補課也。
自學:出墻桃自媚,穿屋筍猶鮮
此乃先生在隨筆《金字塔外:死與蜜糖》中引用的贈給友人的一聯。此文立足生死高度,中外典籍信手拈來、行文左右逢源而自如輕松,其根底自然還在于古文與外文的基礎。而“桃出墻”、“筍穿屋”的意象,也正是先生“不拘一格”的心理外化。
“只要觸角所及,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、入木三分”——看著有關專題片對饒宗頤的紹介,筆者想到了通曉數學、物理、生理、地質等學科的畫家、雕塑家、音樂家、發明家、天文學家、建筑工程師達芬奇。后人稱饒先生為“東方達芬奇”真是恰如其分。而且,這兩位通才的共同特點在于:超凡持久的自學能力。
“凡有所學,皆為性格”。正因為隨心所欲,乘興而發,即用即學,所以后人很難把饒宗頤先生歸到哪一“家”,他曾幽默地說,“我是一個無‘家’可歸的游子”。
的確,文革中大陸學者顛沛流離,饒宗頤卻在滿世界“自學”:考證甲骨文,他東渡日本;研究敦煌學,他遨游法蘭西;研究梵文,又去了印度——1978年退休至2018年馭鶴,整整四十年,他的“自學”與“治學”步步精進、相得益彰。
而且,“游子風”與“自學”、“自由”、“自在”實在是唇齒相依。有論者評得到位:“他有三顆心,第一顆叫好奇心,第二顆叫孩童心,第三顆叫自在心,一顆比一顆高”。可以說,先生的“自學”,學的絕不僅僅是經史子集,更多的還是充滿尊嚴與智慧的“活法”。羅素說過:“對愛情的渴望,對知識的追求,對人類苦難不可遏止的同情心,這三種純潔而無比強烈的激情,支配著我的一生。”可見中外哲人心氣相通。
2008汶川地震,饒宗頤書“大愛無疆”四字,籌得500萬元。2010舟曲特大泥石流,正在敦煌慶賀95華誕的先生將160萬壽禮慨然捐贈災區。2013雅安地震,先生“戚戚之情,哀哀我心”,“現捐款50萬元港幣以表微衷。”
求知欲與大愛、與惻隱之心密不可分,也正是饒宗頤先生留下的寶貴遺產。
總之,先生的家學是“五管齊下”的家學,先生的“華學”是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本土學問,先生的自學是“隨心所欲不逾矩”的“無法之法”。這三點對于犖犖后學的啟迪,彌足珍貴。
“天地大觀入吾眼,文章浩氣起太初”。面對“曠世奇才”、“東洲鴻儒”、“漢學泰斗”、“國學大師”的稱謂,九旬饒老莞爾:“呵,大師?我是大豬吧。現在‘大師’高帽滿天飛,太多了。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,我可不敢當。”潮汕話里,“大師”與“大豬”諧音。
“如可贖兮,人百其身”。無疑,像饒先生這般學問、人品俱佳的大學者的離去,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空白。我們所能夠做的,當是尋源“太初”,報答“天地”。